【側記】2023花蓮影音學堂大師講堂-林木材【紀實影像的邊界與穿越】
日期:2023.04.22 19:00
與會來賓|電影文字工作者林木材
文字|孔祥珩、張志宏
攝影|張玳瑋
#鐵電紀實 #花蓮影音學堂 #大師講堂 #林木材
上周六4/22夜晚,影音學堂的學員們與我們共度了一堂紀錄片的進階課程「紀實影像的邊界與穿越」,雖然小編很想將課堂上的點點滴滴藉著側記傳達給無法到場的大家,但是,林木材策展人是藉由許多影片範例來擴展大家對於紀錄片定義的想像,這些影像實在是很難只透過文字來言傳,不過小編有貼心地幫大家附上相關影片的預告,請各位搭配側記來同時服用喔。
這告訴我們不能因為鐵電小編側記做得好,大家就可以在家翹腳等側記啊!每堂影音學堂大家還是得親身到場,才能不錯過任何的課程精華、才能貼身領略講師風采、才能課後與大師簽名合照呀!

#紀錄片如何被定義及反思其定義
課堂一開始,林木材策展人先拋出兩個問題,分別是「大家最近有看什麼紀錄片?」及「一部好的紀錄片應該具備什麼條件?」認真的學員踴躍回答之後,林木材提出了好幾個關於紀錄片的定義。
例如,1926年英國導演John Grierson提出「紀錄片是對真實事件做有創意的處理」,這解釋的範圍非常廣泛,什麼是創意?如果我覺得我很有創意,但觀眾看到覺得很無趣,那這還能被稱為紀錄片嗎?那或者是說紀錄片是拍攝現實題材,當過分的有創意會不會造成扭曲?
搬出維基百科裡的定義:「紀錄片是描寫、記錄或著研究現實世界題材的電影。」並扣問如果加上個”非”,變成「紀錄片是描寫、記錄或著研究非現實世界題材的電影」是否也成立?紀錄片可以描寫科幻嗎?可以描寫玄學、鬼神、夢呢?
WIKI的定義接著還有「在大多數情況下,紀錄片不需要演員參與。」我們可以想想,有沒有什麼情況是可以用演員的?例如:當時沒有留下影像,甚至連照片、文字搞不好都沒有,我們可能從哪邊聽到或覺得這東西應該是存在的,此時就有可能會因為需要畫面而藉由演員來演繹這段歷程。
WIKI還提到「在紀錄片中表現的人、地點、情況與現實、實際情況一致。」大家同意嗎?譬如說,現在我請了一群演員去演228事件,可是可能跟當時的狀況不太一樣,因為你時空就是不一樣,那假設紀錄片所表現的內容與這些現實的實際情況不一致,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一部片其實跟現實你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時會有什麼問題?這不就是現在政治的情況嗎?當意識形態不同時,所看到的就會不一樣。
林木材也搬出字典裡的定義:「紀錄片:名詞。立基於真實事件、時代、生命故事,或是其重現,聲稱準確描繪事實且不包含任何虛構成分。」然後一句句推翻,並提到電影史學家Erik Bamouw曾提到「真實感與權威性是紀錄片的命運所繫,無論動機如何,對於利用他們的人來說,這兩點是引誘力,也是對事實進行啟發或者欺騙力量的源泉。」再來舉例各種紀錄片類型及變體,讓學員們瞭解到,其實,所有電影都可說是紀錄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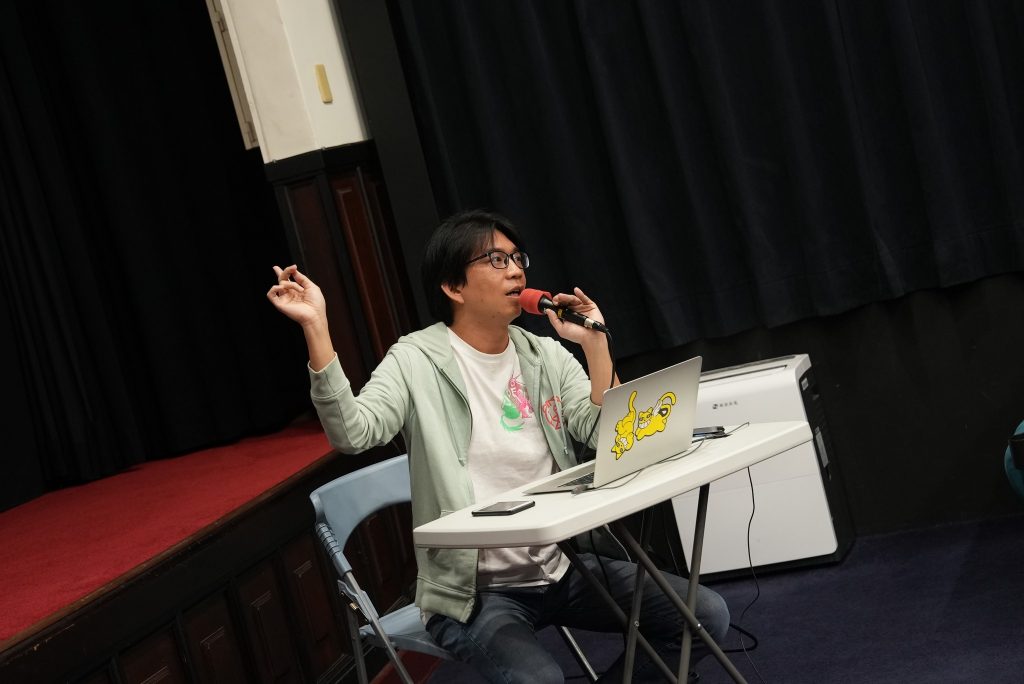
#紀錄片的起源與院線片的原型
大家都知道1895年盧米埃發明電影,林木材藉由《工廠下班》的影像,先讓大家去思考在影片中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有學員提到速度較快,林木材回應其膠卷拍攝時是一秒24格,可是放映時會把機器調整成一秒18格,所以影像就變快。當時大部分的電影,都是在白天拍攝,因為需要光,但工廠下班多半在傍晚,所以導演就跟他的親朋好友們說,我發明了一個可以拍東西的動態影像機器,我想拍工廠下班,你們可不可以去這個地方,然後演一次工人下班的情況?當時的人都還不知道電影,但他們就想說這是一個很大的事件,所以就造成明明是演繹下班的情況,反而變成盛裝出席。
其實在盧米埃兄弟發明電影之前,也有其他人發明動態影像的紀錄,可是只有盧米埃兄弟跟觀眾收費,所以他就成為一個電影觀影最早的商業行為,就是所謂院線片的原型。
延伸資料:《工廠下班》
#水澆園丁與場面調度
從盧米埃兄弟的另一部作品《水澆園丁》來看,這部作品即與《工廠下班》與《火車進站》不太一樣,雖然鏡頭仍舊沒有移動,可是片中的人在動,所以導演跟片中兩個演員說明景框大小,讓演員知道表演的範圍與位置,從這部片中可以看到「場面調度」,甚至也可從中看見腳本設計的概念。
延伸資料:《水澆園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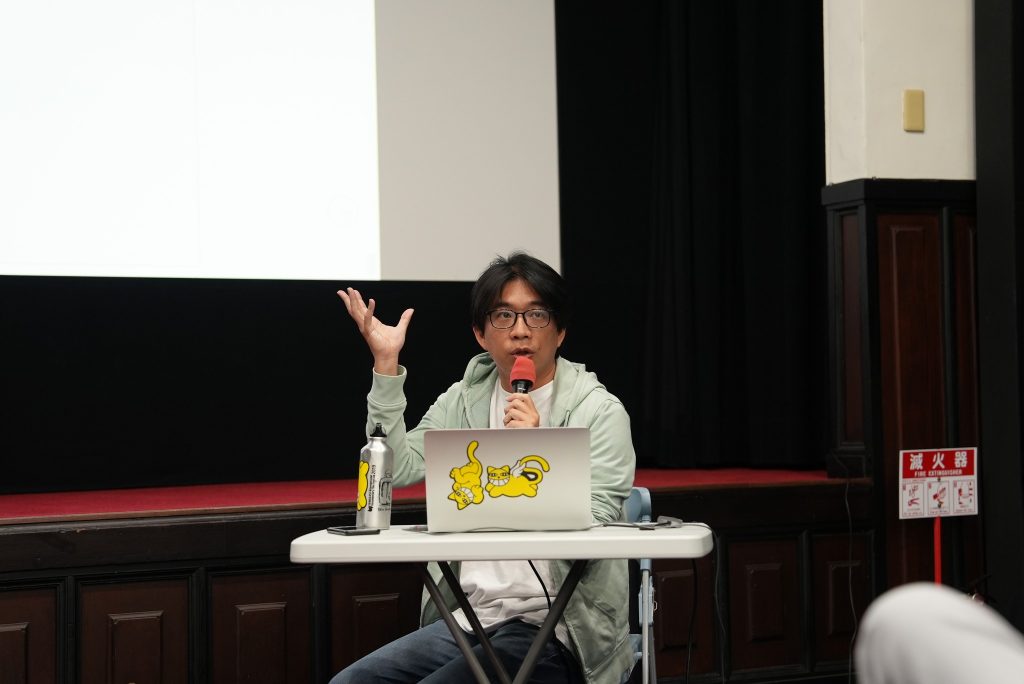
#用創意觀點去呈現貧困裡的智慧
再來,林木材秀出1993年海蒂.哈妮曼的作品《金屬與憂鬱的國度》,描述90年代祕魯因經濟通膨、腐敗官僚與反政府游擊活動促使兼差計程車司機成為最時興的全民運動。
要描寫貧窮經濟狀況可以有許多方式,有些導演會嚴肅處理,可能就會去做政治討論及經濟分析,而海蒂.哈妮曼則是帶著劇組坐上不同計程車,一一訪問不同司機的故事。其中一個經典片段,就是導演發現一名計程車司機的車非常的破裂,就請這名被攝者介紹自己的車,形成了一個很特別的關係,然後這名被攝者發現有人要拍,就很開心地介紹著他破爛到不行的車子,明明看起來很貧苦,卻也展現出某一種面對貧窮現實世界的智慧,展現出一種演繹關係,也從中可以看見創意型的觀點存在。
延伸介紹:金屬與憂鬱的國度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43613
#一部不需要攝影師的電影
再來秀出2014TIDF的影片《馬德里獨白》,這是一部不需要攝影師的電影,導演運用Google街場搭配旁白不斷切換畫面,這算不算是紀錄片呢?其實這就像是用照片講故事,紀錄片一定要是動態影像嗎?像這樣的靜態影像可以嗎?搞不好導演就是給觀眾看他的電腦螢幕,然後他就在旁邊按一個錄音鍵,滑鼠點一點,然後把話講完,影片也隨之製作完成,而這部片在本質上仍是紀錄片。
不過Google可能即將取消街景服務,林木材提到其實知道這消息時是有點傷心的,其實街景服務是可以回去看不同時間的街景,可以回去看自己的家以前的模樣,這也是一種紀錄。
延伸介紹:《馬德里獨白》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3050

#憑導演主觀重組素材
擴張了「紀錄片」的定義之後,林木材接著放Jean-Gabriel Périot於2007年的作品《二十萬個亡靈》,影片由廣島原爆前後與重建完成的一系列的拍攝素材所組成,在不斷疊生的影像與音符中,導演有意識地以「原子彈爆炸圓頂屋」的位置來重組疊上不同年代的素材,以呈現導演觀點。
延伸資料:《200000 PHANTOMS》
接續介紹的是艾倫.柏林納導演的作品《絕對清醒》,本片談的是失眠,導演用了很多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也就是導演到處蒐集各個年代各種影片裡的關燈的片段,將之組在一起。
延伸資料:《絕對清醒》(Wide Awake)
咖啡時光:《絕對清醒》映後座談
https://www.tidf.org.tw/zh-hant/reportsandarticle/1862
同樣是艾倫.柏林納導演的作品《以遺忘為詩》,導演以長達五年的時間紀錄下表舅在生命晚年被阿茲罕默症逐漸奪走的人生智慧與記憶,用本片來探討「紀錄、存在、記得、記憶」等命題。
延伸資料:《以遺忘為詩》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273

#紀錄片倫理
經過上半場的各種推翻傳統紀錄片定義的各種形式紀錄片,下半場講堂進入更進階的紀錄片倫理探討。首先談論的是吳米森的《九命人》,影片裡其中一段師生錄音,木材請大家猜猜到底是真是假?而被錄音的老師又是否知道學生在錄音?而此段素材是真實還是重演是否又會影響觀眾的觀感?而紀錄片倫理在林木材看來,紀錄的對象不同、關係不同,倫理的標準也不同,拍攝紀錄弱勢族群的話,自然倫理的標準就會提高。
延伸資料:《九命人》
https://docs.tfai.org.tw/zh-hant/film/4096
#預設與重新詮釋
接著放映萊拉.巴卡尼娜的作品《關於人生的短片》,影片內容拍攝足球場上的PK大戰,鏡位看似隨意擺在那完全沒有動,但在這短暫的2分鐘裡,卻在這定鏡的景框中看見最後的戲劇轉折,以及裡頭角色間的情緒變化。
延伸資料:《關於人生的短片》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63450
而《萬蟲之聲,繁星之光》)則是在日本政府宣佈福島地區重新開放時,西川智也導演把一捲100呎長的35釐米膠卷,埋在福島一號核電廠25公里附近,直到隔天日出取出。蟲聲與星光,都成為膠卷上的印記。膠捲放出看來像是輻射的畫面,算是導演的控訴。但這難以證實是輻射的東西,算是「真實紀錄」嗎?但所被記錄下來的蟲聲星光又是「貨真價實」的。
延伸資料:《萬蟲之聲,繁星之光》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20573

#實驗電影小歷史
此時有觀眾不禁提問,所謂「錄像藝術」與「實驗電影」的分野?
林木材於是幫大家補上一段實驗電影歷史課,所謂「實驗電影」在早年是在拍攝內容上做實驗,譬如說梅里葉拍攝攝影師變魔術,利用蒙太奇製造虛實交錯感。但之後就演變成是在對「膠捲」本身做實驗,比方說用紅茶沖印底片,用以呈現不同效果來創作。但在電影數位化之後,「實驗電影」跟「錄像藝術」兩者就開始有交疊,但是實驗電影的本質是對電影做實驗,舉例來說,安迪·沃荷在1963年有部作品是《睡眠》,以長鏡頭拍攝情人睡覺長達5個多小時,這是一種實驗,因為當時拍片不像現在數位化要拍多長的影片就有多長。
而70年代出現擴延電影(Expanded Cinema)的概念,像是多重投影,或是用不同速率的投影機來投射電影等,依然算是實驗電影。
另外林木材也推薦大家近期有去台北的話,可以去北美館觀看高重黎的展覽(https://www.tfam.museum/Exhibition/Exhibition_Special.aspx?id=729&ddlLang=zh-tw)。
延伸資料:擴延電影(Expanded Cinema)
https://edumovie-tfai.org.tw/article/content/364
#沒有畫面的影片
安潔莉卡.荷塔2015年的作品《最好是這樣》,影片沒有畫面,導演收集了視障者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運用像是google、siri冰冷的語音,讓觀眾體驗及想像視障者的生活。
延伸資料:《最好是這樣》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20567
#重新演繹的歷史
最後介紹的是彼得.克瑞克斯2009年的作品《烹煮歷史》,片名有個雙關語,一個是「烹煮」這件事的歷史,另一則是把歷史拿來烹煮(質疑重組),全片用戲謔的手法重演一段經歷。此時,劇情片、紀錄片、實驗片的分界已逐漸模糊。
延伸資料:《最好是這樣》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43601

#拍攝者該不該出手
有觀眾提問像在《迷霧中的孩子》,拍攝苗族赫蒙的村落裡盛行「搶婚」習俗,導演到底能不能出手相救?木材回答那片導演雖然有某種程度相救,但還是沒放掉她的攝影機。在紀錄片倫理中,當有人身生命安全,當然是比拍片還重要的事。
在觀察式的電影中,像是「直接電影」,強調自己的拍攝就像是牆上的蒼蠅,靜靜地觀察這一切;也有另外像「真實電影」要跟被攝者很熟悉。
延伸資料:《迷霧中的孩子》
https://www.tidf.org.tw/zh-hant/films/110068
延伸資料: 直接電影 Direct Cinema / 真實電影 Cin’ema V’erit’e
https://edumovie-tfai.org.tw/article/content/370
#自由廣場
林木材策展人最後放了部自己口中的「習作」《自由廣場》,用這部曾入選「2020 台北金馬影展-華語透視界」當作Ending,本片透過影音調度來呈現「後威權時代」,觀眾也很有興致與導演討論了本片的手法及拍攝過程,結束了充實的紀錄片之夜。
延伸資料: 林木材導演作品《自由廣場》
https://docs.tfai.org.tw/zh-hant/film/6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