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聊版主:Mango (花蓮鐵道電影院映演夥伴)
▯側記:潔色米
▯攝影:張志宏
版主 Mango的話
在側記開始前,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介紹這部電影的文字,這是Mango在決定選擇《花神咖啡館》來鐵電和我們聊聊時,所寫的心得推薦文:
「一部讓你停下來、感受當下、正視心中小野獸的電影
沒有花、沒有咖啡,只有一首愉快尋常的小曲子,在你耳邊揮之不去
沒有勵志、沒有暖心,只有無盡的擁抱,讓你想吼叫卻發不出聲音
沒有流暢敘事,只有破碎片段來回縈牽,往心底重擊
人生有時好像看場電影就好了,
散場後留下一些自己的片段、帶走一些片中的,繼續前進。」
Mango說,今天這部片子很適合看完後感覺自己被(電影)重重撞擊過,全身和腦袋都塞滿東西,很混亂的走出去,然後昏昏的回家自己待著,因此今天的漫聊風格大概就會像這部電影本身帶給觀眾的觀後感那樣,也許有點斷續不流暢、有點意識流,而我們就在這樣的感受和氛圍下,分享一些看這部電影的心得、彼此感染對這部電影的感覺。
「圖文不符」的電影名稱&音樂元素
音樂的元素在這部電影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片中常出現的那首歌曲〈花神咖啡館〉,貫穿了兩段看似無關的故事,對幾位主角有著代表性的象徵意味,也因此電影的名稱才會以這個在劇中完全沒有出現過且與故事情節毫無關聯的場景命名。
原來這個「花神咖啡館」,不是地名而是曲名。在提到「花神咖啡館」時,大家通常先想到的是那個曾吸引許多文學家、藝術家和名人駐足的百年巴黎咖啡店, Mango在這邊為我們釋疑:英國電子音樂家馬修.赫伯(Matthew Herbert)曾在這間咖啡館做了一首含大量手風琴音的曲子,就取名為〈花神咖啡館〉,而瓦利導演聽到這首曲子非常喜歡,甚至進入一個無法言說的狀態,於是決定要為它拍一部電影,並且以此曲命名,就這樣結成地名、曲名、電影名三位同體的一個緣分了。
瓦利導演本身也是一個DJ,對音樂的敏感度高,其風格喜歡用一些會讓大家進入某種心流、沉浸性很重的音樂;剪接方式也是很有意識的要讓觀眾感受這些東西,常常會在某個情緒高漲的情節下急停,或是立刻轉入下一個場景。Mango分享她看完這部電影後最深的兩個身體感受:一是感覺很像整個人沉在泳池裡;二是很想尖叫但叫不出來的那種巨大壓力,而這兩種意象正是電影中很常出現的畫面。

沒有絕對的傷害者與受害者
《花神咖啡館》中,導演用了2012年和1962年兩個不同年代與時空背景的事件來探討「愛」跟「放下」。Mango說起自己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是不太認同劇中男主角安東的;但後來再慢慢看,慢慢覺得每一個角色都有其在那個位置上的掙扎,有美好回憶的地方,然後有現在的痛苦,也有他未來的選擇,即使是出軌的安東,他也因承受著對情感及靈魂伴侶的矛盾疑惑而不快樂(甚至尋求心理諮商)。
雖然我們可能比較容易對某些角色感同身受(例如:安東的前妻卡蘿),但若把兩段故事串在一起看,或許會發現沒有一個絕對好或不好的角色,裡面有不同面向的糾葛與掙扎,還有好多種模式和關係的愛,像是爸爸/媽媽與小孩、愛人、前妻、婆家對前媳婦、甚至是情敵…大家好像可以在裡面看到某個影子、某個自己的經驗,然後發現自己以前那樣想,但現在也可以不這麼想。「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都看到的話,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更大的眼界來看這些關係?」Mango如此問道。而現場有位二刷這部電影的觀眾分享,她此次看完這部片,也覺得跟之前的心境很不一樣:「現在看了覺得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有時候愛一個人的重點並不是愛的結果,而是你付出了這份愛,然後你被這份愛改變,我覺得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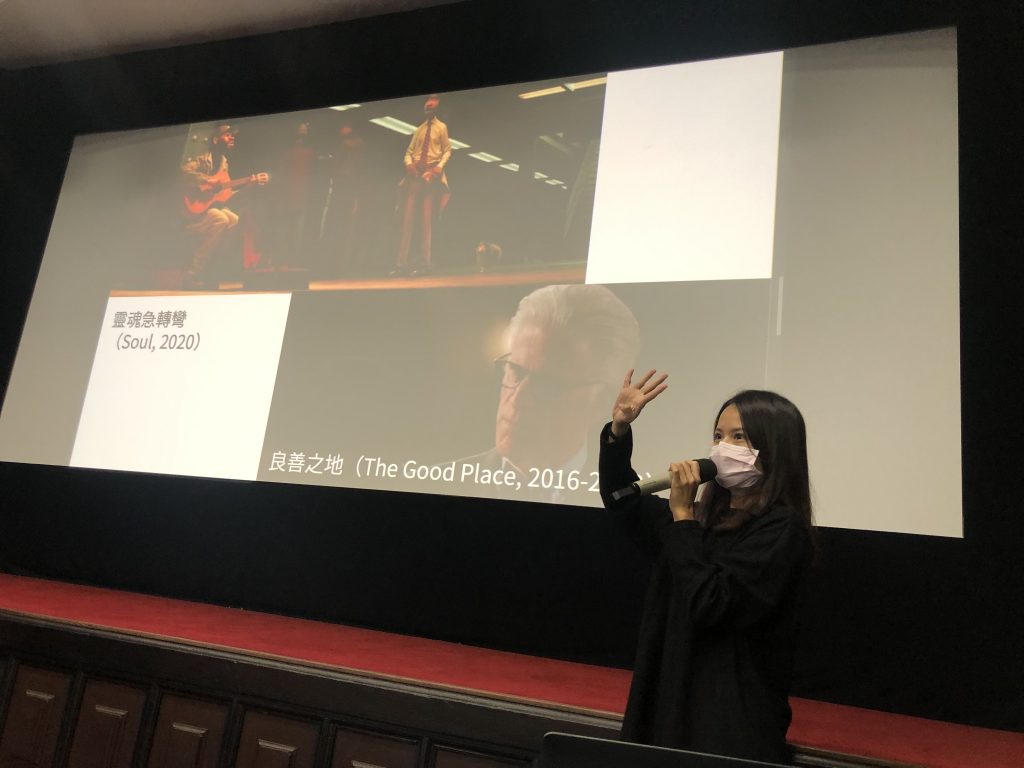
靈魂伴侶是到底什麼?
這部電影著墨很多在「靈魂伴侶」這個主題,Mango首先說明這個字詞起源自希臘神話中宙斯造人及拆解人的故事。普世中大家對於靈魂伴侶的想像常很直覺的放在情侶愛情關係中,但Mango提出幾部也有涉及靈魂伴侶概念的影視作品如《靈魂急轉彎》、美劇《良善之地》來探討關於「靈魂伴侶」更多元的可能性。「只能用在愛情上嗎?」「只能是一對一嗎?」「對象只能是人嗎?書不行嗎?」「只要心靈契合就好,現實考量都不用嗎?」「能不能是有所選擇的?」「能不能產生連結和關係後再變成靈魂伴侶呢?」Mango提出一連串有意思的問題,跳脫原本靈魂伴侶的框架去思考關係。而也許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性,遠比我們所能想能見的還複雜和深遠,就像《花神咖啡館》的電影主視覺海報,乍看是兩人相擁的畫面,其實還有許多隻手環繞圍抱著,而手的主人,可能是意想不到的人。

